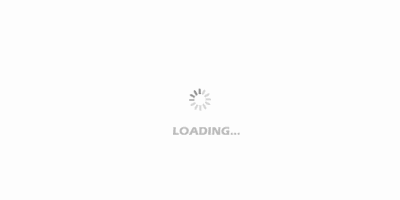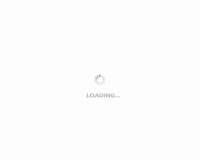第三類結局
我十八歲的時候死心塌地地愛上了一個女孩子,十九歲的時候我又失去了她;到了二十
歲時我終於明白,原來愛一個人並不是只有聚或者散兩種結局。
——題記
下面我要說個故事,雖然我是一個拙劣的說話者,但是我還是固執地相信我完全可以把
這個故事說完,因為芸兒曾經說我的文學底子還不錯。我一向相信她的話,從遇見她的
第一天起。絕對相信。
我是在遇上芸兒之前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亦即是唯一一次失戀後的第八個月左右認識
芸兒的。插句題外的話,那次失戀對於我來說絕對是一場災難。
時候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理由就從我身邊斷然離開的,而且忽略不計了我的所有一切挽
救。當然必須聲明的是,我始終都沒有因為認識她而後悔過,因為她實在是一個非常p
erfect的女孩子,如果她沒有那樣莫名其妙地離開我的話。那是她在我看來的唯一缺點
,以至於半年後她因為某種難以治癒的病症從我的生活中永遠地消失之後,我總是會懷
疑如果她從這個世界消失時依舊是我的戀人,我一定會因為她的曾經存在而終身不娶。
當然,既然她當時已經不是,這個問題也就不存在,我依舊在燕園裡肆無忌憚地欣賞著
身邊經過的每一片風景。然後,在很長一段時間的消沉之後,
那是大二剛開學的時候,一個秋日的傍晚,有很紅很紅的夕陽,有很淒涼很淒涼的落葉
,反正是很美的氣氛,我卻在那樣的傍晚像只沒了頭的蒼蠅似的騎著我那輛價值絕對不
超過30元人民幣的破車在那麼有詩意的林蔭小道上亂竄。我的確也很有負罪感,而且我
也實在不想在那樣的情況下擁有那麼高的回頭率,但很無奈的是,我必須在十分鐘內把
某些應該是比較重要的東西交到系裡去,而恰巧我竟然根本不知道系裡辦公的法學樓究
竟在哪兒。
當然,幾乎誰都已經可以想到,這時候芸兒出現了。我實在不想描述芸兒當時的樣子。
因為直到今天,我依舊為我在那樣美好的一個下午和她那樣在北大日漸稀少的MM說話而
後悔不已。
我當時穿著拖鞋踩著舊車鬍子比頭髮長而且襪子上還有兩個碩大無比的洞。雖然那以後
我極力補救,譬如換了輛還算新的車,而且見她時儘量不穿有直徑超過五釐米的洞的襪
子,等等等等,但她總還是會時不時地回憶起那天下午我的樣子,然後再笑著挖苦我幾
句。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可是我還是盡力注意自己的形象,雖然明知與事無補。大
約人就是這個樣子的,有時候根本就不知道在些為什麼而補救卻依然一樣執著。
“哎,同學,請問法學樓怎麼走?”我很恰到好處地把她攔在了某個十字路口。
“法學樓?我不知道啊。”到這兒完全可以結束一次比較經典的對話了,可是她偏偏又
歪著頭想了想,然後又突然笑著指了一下某個方向,“也許是那兒吧!”說完,她看了
看沒有什麼反應的我,說:“怎麼?不相信嗎?我的直覺一向很准的啊!”
當然,我絕對相信,只是看著她那在晚風中輕輕飄動的長髮走了神而已,更何況這樣的
一個女孩子說她的直覺很准呢?所以,當我十分艱難百般狼狽千辛萬苦地繞了一大圈趕
到系裡卻因為終究還是遲到了好一會而受到領導的質問時,我向他甜甜一笑,給了他一
個合理得簡直無法再合理的解釋:“直覺。”我直到現在也無法理解他當時目瞪口呆的
表情。就那種智商,當年怎麼考上北大的?
然後,
就叫芸兒,所以她在我們宿舍的名字就叫“我長髮的姑娘”。我這麼喊,大家於是也都
這麼喊。我反正是無所謂的了,因為她絕對不是我的個人財產,反正沒有人會懷疑我是
絕對追不上她的,包括我在內。這完全是拜我的那位戀人所賜。自從她的離開,我已經
沒有那麼多盲目的自信了。如果說我的學習成績曾經很棒,畢竟有一張泛著黃的北大錄
取通知書還可以作為證明,但是現在大約只有幾乎就要到手的補考通知書可以作為反例
了。同理,如果說我的古漢語水準還高出儕輩,那麼總是把“綠楊煙外曉寒輕”的下句
記成“天涯何處無芳草”又究竟算是什麼玩意?反正我是不敢對芸兒有什麼奢望了。
了曾經的她不知是為了什麼原因之外,其餘的MM在我這樣的人的生活中無疑都應該是過
客。好在燕園很大事情也很多,再一無是處的混球也照樣可以活得比校長還要忙忙碌碌
,所以我也就漸漸地淡忘了那個“我長髮的姑娘”了,就像淡忘所有應該淡忘的一樣。
當然,芸兒還是應該在我的故事裡出現的,不然我現在也就只有“全文完”三個字可以
說了。其實,我不得不承認她的出現純粹是個巧合;那絕對不是我刻意安排的。大約在
十月份的時候,我們英語四級的哪個班的老師們不知是因為出國還是因為別的什麼狗屁
倒灶的事情反正就離開了。於是我們班也就被臨時打散,作為雜牌軍混編進其他班了。
我和宿舍的另一位大哥被分進了L20班。儘管為了這事我們兩個在當夜宿舍的臥談會上
罵了足足有20分鐘,但是第二天一早我們還是開開心心地背上小書包去上課了。既然已
經這樣了,還不早一點去看美女。豈不是要蒙受雙重損失?!那麼,按照故事的發展,
我理所當然地應該見到芸兒,可是很遺憾的是,我在教室裡傻傻地直坐到上課也沒有見
到芸兒。因為,她遲到了。
然後,就是整整三天的殫思竭慮的籌畫,而籌畫的結果就是在週五上課時,當芸兒伴著
上課鈴聲走進教室時別無選擇地坐到了我的身邊。那天上課以後,芸兒還為這事情問過
我,說為什麼那天最後一排最偏僻的角落都坐滿了人卻偏偏只有你身邊的那個位置空著
而且剛上課不久那些人就都全溜了呢?我高深莫測地說了一句,知道什麼叫緣分嗎?芸
兒嘴角一撇,不屑地說,我只信緣,不信份。我像是第一次見到這個女孩子似的,呆呆
地看著她。她以為我不懂,就解釋說,某天某年某個地方我在哪兒遇到你,那叫緣,我
沒有辦法左右;但是遇到了你以後的事情我只相信自己。我真呆了。就在那天,我知道
她叫芸兒,數學系的。然後我就說,你叫我梅川吧,因為我的網名就叫梅川伊夫。芸兒
愣了一下,然後就笑了起來,你沒穿衣服還敢坐在這兒上課?她就趴在桌子上笑啊笑啊
,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卻又不敢笑出聲來,只把滿頭的長發笑得飄來飄去,發梢間一陣
陣的清香也在空氣裡飄來蕩去。回到宿舍,他們都故意很不屑地說,就是那個傻丫頭?
我也就故意 很沒好氣而且很陶醉地說裡一句,沒見識也別瞎說,那叫純真。
當然大家不說我也知道,他們和我一樣在拿芸兒和她做比較呢。雖然大家總喜歡拿我開
涮,可是大約一年前她唯一一次來過我們宿舍之後,大家什麼都沒有評論。那次她是因
為來拿一本書吧,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反正她不喜歡和我在別人面前出雙入對,因為
嫌太招搖了,結果整個學校也沒有幾個人知道我竟然和她在一起,害得不知什麼系的男
生還依然寫了幾封情書給她。唉,還想那麼多做什麼?自己還不夠傷心嗎?我搖了搖頭
,又歎了口氣,然後就睡覺去了。
以後的英語課,班裡的兄弟們當然是不方便再去捧場了,但是我和芸兒也竟然漸漸多出
了許多默契,總是會坐到一起,話題也漸漸地多了起來。一次英語課上,老師講著講著
就申發開去了,自然而然地扯到了愛情的話題上去了。那節課我就聽到這兒了,因為緊
接的時間我就和芸兒瞎白話過去了。芸兒問,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我沒有說話,點了
點頭。她就說,你有嗎?我還是趴在桌子上,烏黑烏黑的大眼睛就那麼近地盯著
我;我忽然覺著一絲緊張。沒有,我鎮定了一下說。她還是很平靜地問,那麼,曾經有
過嗎?我聞著她的發香,心裡也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在輕輕蕩漾,但還是淡淡地說了
一句,有過的。芸兒還接著問,她怎麼樣的?我愣了一下,就還是懶懶地笑著,像是不
經意地說,她?很好啊。很好?芸兒笑了,那你們怎麼分開的?我忽然就坐直了起來,
轉過頭狠狠地盯了她一眼,但突然間又不知為什麼覺得十分洩氣,歎了口氣又轉過頭去
,也不說話了。芸兒嚇著了似的,整個人向後一縮,然後才醒悟過來似的,連忙道歉說
,我不是故意的,別生氣,好嗎?求你了,千萬別生氣啊!我還是沒有抬頭,歎了口氣
,說,沒什麼,真沒什麼的。她還是不放心,追問著,真的?我抬起頭,又像以往一樣
不在意地笑著說,真的。芸兒這才放心似的,搖著我的手,笑著說,你剛才嚇死我了,
從來都只見你笑著的。
她似乎沒有覺得什麼,但我卻立刻一陣慌亂,然後什麼都沒想,左手就輕輕掙脫出來,
她這才一驚,臉頓時就紅了。我這才想到要說些什麼掩飾一下,可是又實在什麼都想不
出來,於是就是兩個人的沉默。我對自己不加考慮的行為立刻就感到後悔。其實也沒有
什麼的,芸兒也許抓起我的手時什麼都沒有想,自己為什麼就這麼敏感呢?難道就因為
想到了想起了初戀的時候第一次抓起她的手,她卻像今天的我一樣輕輕地掙脫了開去?
唉,我在心底不由自主地歎了口氣,然後轉過頭去,向芸兒擠出一絲勉強還算自然的笑
容,怎麼,不是想知道我和她分手的原因嗎?這次卻是她沒有轉頭向我,只說了一句,
不想。我苦笑了一聲,不想也好,其實就是你想知道我也說不出的。芸兒這才驚訝的轉
過頭來,怎麼會這樣的?我搖搖頭,平靜地說,在99年元旦的夜裡,她留下了一封莫名
其妙的信,然後我就再也沒有能夠和她聯繫上。事實上,當天夜裡我在她們樓下冒著雪
站了一夜,可她甚至都沒有從窗戶裡看我一眼。芸兒接著問,她現在呢?我笑了笑,不
在了,絕症。芸兒一愣,長長地歎了口氣,過了好久才說,其實你應該為她想想的,也
許她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後不想給你負擔呢?我說,有必要嗎?芸兒很認真地說,會啊,
也許在你看來這個想法很可笑,但是如果她真的喜歡你,只要是她看來對你好的事情她
一定會努力去做的,真的。我沒有說話,芸兒就接著說,我以前就有一個朋友,愛她男
朋友愛得死去活來,但是最後得了白血病,她就狠狠地踹了她的,我問她為什麼
,她說這樣那個男生會在以後的日子裡忘了她,繼續快快樂樂地生活。我笑了笑,輕輕
地搖了搖頭,還是不說話。芸兒見我這樣,也就不說話。直到下課以後,我已經收拾好
書本就要離開時,芸兒才又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問我,她最後那封信都說了些什麼?
我剛想回答,卻不知怎麼就冒出了個惡作劇的想法,大聲說,五個字,我們相愛吧!教
室裡,大家本來都在準備離開,聽到我的話都是一愣,接著就都大笑起來。芸兒立刻就
明白過來,在我肩膀小心地大了一下,說,你好壞啊,不理你了啦!然後就紅著臉笑著
跑開了,留下了笑著的大家和我。我笑啊笑啊,但是其實,那個時候,我實在是想哭,
便扭過了頭去,然後悄悄走開。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獨自去了未名湖邊。剛到燕園時逛未名湖,有老爸老媽陪著;後來
呢,就是她陪著;而現在,我身邊誰也沒有。從許久之前,我就再也不想經過所有曾經
的過往,可是現在又要勉強自己去想起她和所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認芸兒的話實在是
很讓我震撼,雖然曾經也有人那麼說過一些類似的話。但是,芸兒的話讓我決定要好好
想想,好好地想想。
其實所有的一切依然是那麼清晰,我始終也都沒有能夠忘記什麼。如果說故意想忘記些
什麼的話,可能是因為她的絕情,而現在也許還多著個尷尬的芸兒。當然,想到芸兒,
我就更加要承認,無論是什麼原因,如果她是在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之後才斷然離開我的
話,那麼這種離開對於我來說都一定是莫大的恩賜。因為,雖然她的生命就像是花瓣上
的朝露一樣在離開我之後就匆忙地消逝了,而我卻依然在幾許遺憾和感慨裡還算是快樂
地生活著。可是,她知道自己的病嗎?秋意正濃得很,未名湖畔的葉子在蕭瑟的秋風裡
飄落著,飛舞著,跳脫著,似乎想要帶走些什麼,可是又似乎什麼也帶不走。我就在這
風這夜裡默默地回憶著所有的如煙往事。我曾經寫過日記的,可是裡一定沒有任何
的痕跡;而她的每一句話似乎也都和自己的身體毫不相干。別想了,我對自己說,因為
在湖畔的寒風裡我忽然覺得有一些恐懼。那個元旦的夜晚,我在她們樓下冒著風雪的時
候,心裡的苦依然刻骨銘心;但是如果我錯怪了她,她的苦又會是怎麼樣的呢?我的確
怕了。既然找不到證據,就別找了吧,我對自己又一次說。於是,這個念頭在又一個不
眠之夜裡就漸漸地隨著夜風飄遠了。
芸兒當然沒有真的生氣,她的確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但是,我還是以向她賠罪的
名義在週末請她吃了一頓飯,又一起去大講堂看了一場電影。開始,弟兄們聽說我要請
她吃飯,就笑著說,要追女孩子也別用這麼老套的辦法嗎,不如認她做小妹子嘍。我笑
了笑,什麼也沒有說,我對芸兒究竟是什麼感覺其實我也說不清楚。影片結束時已經是
很晚了,然後我說,送你回去吧。她搖了搖頭,看著我,甜甜地笑著說,我們去未名湖
邊走走吧。我沒有說話,只盯著她看,然後突然就笑了。她有些慌,說,你這麼怪怪地
看著人家做什麼?我於是就不笑了,突然就拉起了她的手,把她擁到懷裡,說了一句,
走吧。
終究是北方的秋天,離開上一次來湖邊只是隔了一兩場秋雨而已,卻已經冷了許多
。可是未名湖邊那許許多多的垂柳都還沒有凋殘。秋的蕭瑟於是也就不再那麼淒厲,更
何況抬起頭就可以見到明亮的天空,就因為外面不夜的燈火。我就和芸兒坐在湖邊的長
椅上。一陣風吹過,她哆嗦了一下,我就問,冷嗎?她搖了搖頭,歎了口氣,然後像是
自言自語一樣喃喃地說,咱們就永遠坐在這裡該有多好啊。我笑了笑說,真傻。然後我
們就不說話,靜靜地坐在那兒。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我似乎想了好多好多,卻又似乎什
麼也沒有想。反正,過了好久好久之後,我就突然冒出了一句,我和她也來過這兒的。
芸兒似乎哦了一聲,似乎沒有什麼別的反應,但是我分明覺得她握著我的手動了一下。
又過了一陣子,芸兒說,風好涼,我們回去吧。
以後的好一陣子,芸兒再也沒有和我那麼親密,我也沒有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告訴宿舍裡
的弟兄們我知道他們一定會罵我笨,連哄女孩子都不會。反正有的是事情要做,偶爾騙
騙自己,大約什麼事情都可以忘掉,更何況芸兒也沒有對我不理不睬嗎。
西元1999年12月31日,也就是世紀末的最後一天吧,冷冷清清的宿舍裡就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他們五個都去陪老婆了。聽聽歌,玩玩《三國Ⅶ》,總還是覺得無聊,時間就像
是被砍斷了四隻腳的老烏龜,怎麼也走不動似的。好容易捱到晚上十點來鐘,三角地那
兒的歌聲笑聲喝彩聲就絡繹不絕地響了起來。可是我實在是沒有什麼興趣,尤其對於太
熱鬧或者是太冷清的地方。可是總要找些什麼事情來做吧,我歎了口氣,就決定收拾一
下屋子。床上的收拾好了就收拾床下的,床下的收拾好了之後還有桌子,然後還有書架
,還有抽屜。歎了口氣,打開床前的旅行箱,原來裡面裝的是羽絨服,該穿了吧。拿出
來拍一下口袋,居然有一封信,原來是她給我的最後的文字。還有不到一個小時就要走
進新千年了,該忘的就要忘了,趕快回頭看看吧,也許以後就再也沒有這樣的心情了,
我對自己如是說。於是懷著一種幾乎是懷舊的心情,我又一次小心地打開了那封信。很
簡短的一封信,簡潔得一如她的性格。
“已經是一月份了,你見到了嗎,未名湖畔的垂柳都已經凋零不堪了,這個逝去的秋天
再也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以後,再也別來找我了,好嗎?祝你一生快樂幸福。”
我於是又沉默了一陣子,然後笑著對自己說,再過一會兒,那就是一千年以前的事情了
。然後就聽到電話吵了起來,原來是芸兒。她要我到樓下的信箱裡去取信,然後就掛了
電話。我抱著電話至少發了三秒鐘的呆,這才感歎出一句,千禧新新人類!
信自然是很快就取回來了,封口處的膠水似乎還濕著。我有一種預感,我正在說的這個
故事就快要結束了。但是我還是不明白她要弄什麼玄虛,居然在這個時候來開這種玩笑
,有什麼在電話裡說不就結了嗎?信居然也很簡短。
“梅川,我喜歡你。我說過,我相信緣,不相信份。我不會像我以前的那個朋友丁丁一
樣,把所有的真心真意都埋在心底,然後獨自傷心。如果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喜歡我,我
會在三角地的電話亭等你到0:00。芸兒。”
我大腦裡頓時就只剩空白了。我扔下手頭的所有東西,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只看
了一下牆上的大鐘,還有十來分鐘。我就像是所有經典的愛情故事裡的主人公一樣,毫
不猶豫地沖向三角地,什麼也不想,在擁擠的人群中狂奔,只在這世紀末的最後時刻為
自己浪漫的故事而打拼。越是靠近三角地,人也就越多。大講堂前面居然還臨時搭
了個舞臺,台下還有一口大鐘,很有意思。我當然是不在乎它是否有意思;我要找的不
是它。終於,我看到了芸兒。她就站在路的對面,也正在笑著看著我,一身潔白的衣服
,長髮在風中輕輕的飄動著,眼裡滿漾著笑意。我想走過去,可是路上都是人,而且芸
兒也示意我不用費力過去,於是我就大口地喘著氣,很狼狽的扶著腰,也笑著,全然看
不到來來往往的人,眼裡只有她,我的芸兒。然後,老校長就開始撞鐘了。
“鐺——”“十!——”
成千上萬的人都忽然間安靜下來了,很整齊地喊了起來。芸兒只是笑著,似乎這個世界
只剩下了她和我。我忽然覺得很溫暖,因為終於有一個女孩子可以全心全意地喜歡我,
真心真意的那種。而且,我也是同樣地喜歡著她。這應該是很的事情了吧。
“鐺——”“九!——”
他們都說愛情只有兩種結局,一就是徹底的散,再就是完全的聚,簡單到不能更簡單。
對於曾經的她,也許我的確是徹底的散了;而對於芸兒,除了愛,還能有些別的什麼?
…… ……
“鐺——”“三!——”
我終於有些清醒了。就快要過千年了,就快要告別單身了,對著芸兒的笑容,相識時的
情景也在不經意間浮現,而以往的一切也都在電光火石間從心裡掠過。
“鐺——”“二!——”
未名湖畔的柳樹已經凋零不堪了……再也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我以前的那個朋友
丁丁……以後再也別來找我了……把所有的真心真意都埋進心裡……我是數學系的……
“鐺——”“一!——”
我終於知道原來許多故事的結局都是有可能在最後一秒發生不可思議的變化的了。我說
的這個故事也不例外,雖然在倒數第二秒之前我根本就沒有預見到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鐺——”
世紀末的鐘聲終於在一千年的漫長等待後敲響了,大家都在歡呼著,雀躍著,釋放著所
有青春的激情和感動。而我卻狂奔在不知會通向哪兒的路上,也顧不得去多想離開時芸
兒那張流著淚的美麗臉龐。那已經不再重要了,我癱在自己的床上對自己說。
元旦之後的英語課我都沒有上,反正也沒有幾節了;他們說芸兒也沒有去上。四級考試
我和她也不在一個考場,於是也就錯過了那個學期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等到再次見到
她,已經到了大三的上半年,也就是不久之前我剛過完二十歲生日的一天。還像是一年
前初次見到她的那個秋天一樣,天很藍,雲很白,秋風下的落葉也很瀟灑,只是芸兒的
身邊已經多了一個英俊高挑的男生。我不由地一陣失落,依舊是穿著自己的破襪子,踩
著比原先又舊了許多的單車,從短髮的她的身邊悄然經過。我沒有回頭,她應該也沒有
。多好的一個女孩子啊,我忽然就笑了。
後來,終於有個朋友問了我一次,你究竟為什麼在最後又放棄了芸兒呢?我笑了笑,說
,其實也沒什麼的,然後就轉過身去,差點兒流下淚來。其實,答案很簡單,卻是我和
芸兒都不曾想到過的。我曾經的那個讓我刻骨銘心的戀人有一個和她一樣美麗的名字叫
做汀芷,而她數學系的同學們則給了她一個更加好聽的名字叫做——丁丁。
(全文完)
於是我們班也就被臨時打散,作為雜牌軍混編進其他班了。
我和宿舍的另一位大哥被分進了L20班。儘管為了這事我們兩個在當夜宿舍的臥談會上
罵了足足有20分鐘,但是第二天一早我們還是開開心心地背上小書包去上課了。既然已
經這樣了,還不早一點去看美女。豈不是要蒙受雙重損失?!那麼,按照故事的發展,
我理所當然地應該見到芸兒,可是很遺憾的是,我在教室裡傻傻地直坐到上課也沒有見
到芸兒。因為,她遲到了。
然後,就是整整三天的殫思竭慮的籌畫,而籌畫的結果就是在週五上課時,當芸兒伴著
上課鈴聲走進教室時別無選擇地坐到了我的身邊。那天上課以後,芸兒還為這事情問過
我,說為什麼那天最後一排最偏僻的角落都坐滿了人卻偏偏只有你身邊的那個位置空著
而且剛上課不久那些人就都全溜了呢?我高深莫測地說了一句,知道什麼叫緣分嗎?芸
兒嘴角一撇,不屑地說,我只信緣,不信份。我像是第一次見到這個女孩子似的,呆呆
地看著她。她以為我不懂,就解釋說,某天某年某個地方我在哪兒遇到你,那叫緣,我
沒有辦法左右;但是遇到了你以後的事情我只相信自己。我真呆了。就在那天,我知道
她叫芸兒,數學系的。然後我就說,你叫我梅川吧,因為我的網名就叫梅川伊夫。芸兒
愣了一下,然後就笑了起來,你沒穿衣服還敢坐在這兒上課?她就趴在桌子上笑啊笑啊
,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卻又不敢笑出聲來,只把滿頭的長發笑得飄來飄去,發梢間一陣
陣的清香也在空氣裡飄來蕩去。回到宿舍,他們都故意很不屑地說,就是那個傻丫頭?
我也就故意 很沒好氣而且很陶醉地說裡一句,沒見識也別瞎說,那叫純真。
當然大家不說我也知道,他們和我一樣在拿芸兒和她做比較呢。雖然大家總喜歡拿我開
涮,可是大約一年前她唯一一次來過我們宿舍之後,大家什麼都沒有評論。那次她是因
為來拿一本書吧,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反正她不喜歡和我在別人面前出雙入對,因為
嫌太招搖了,結果整個學校也沒有幾個人知道我竟然和她在一起,害得不知什麼系的男
生還依然寫了幾封情書給她。唉,還想那麼多做什麼?自己還不夠傷心嗎?我搖了搖頭
,又歎了口氣,然後就睡覺去了。
以後的英語課,班裡的兄弟們當然是不方便再去捧場了,但是我和芸兒也竟然漸漸多出
了許多默契,總是會坐到一起,話題也漸漸地多了起來。一次英語課上,老師講著講著
就申發開去了,自然而然地扯到了愛情的話題上去了。那節課我就聽到這兒了,因為緊
接的時間我就和芸兒瞎白話過去了。芸兒問,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我沒有說話,點了
點頭。她就說,你有嗎?我還是趴在桌子上,烏黑烏黑的大眼睛就那麼近地盯著
我;我忽然覺著一絲緊張。沒有,我鎮定了一下說。她還是很平靜地問,那麼,曾經有
過嗎?我聞著她的發香,心裡也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在輕輕蕩漾,但還是淡淡地說了
一句,有過的。芸兒還接著問,她怎麼樣的?我愣了一下,就還是懶懶地笑著,像是不
經意地說,她?很好啊。很好?芸兒笑了,那你們怎麼分開的?我忽然就坐直了起來,
轉過頭狠狠地盯了她一眼,但突然間又不知為什麼覺得十分洩氣,歎了口氣又轉過頭去
,也不說話了。芸兒嚇著了似的,整個人向後一縮,然後才醒悟過來似的,連忙道歉說
,我不是故意的,別生氣,好嗎?求你了,千萬別生氣啊!我還是沒有抬頭,歎了口氣
,說,沒什麼,真沒什麼的。她還是不放心,追問著,真的?我抬起頭,又像以往一樣
不在意地笑著說,真的。芸兒這才放心似的,搖著我的手,笑著說,你剛才嚇死我了,
從來都只見你笑著的。
她似乎沒有覺得什麼,但我卻立刻一陣慌亂,然後什麼都沒想,左手就輕輕掙脫出來,
她這才一驚,臉頓時就紅了。我這才想到要說些什麼掩飾一下,可是又實在什麼都想不
出來,於是就是兩個人的沉默。我對自己不加考慮的行為立刻就感到後悔。其實也沒有
什麼的,芸兒也許抓起我的手時什麼都沒有想,自己為什麼就這麼敏感呢?難道就因為
想到了想起了初戀的時候第一次抓起她的手,她卻像今天的我一樣輕輕地掙脫了開去?
唉,我在心底不由自主地歎了口氣,然後轉過頭去,向芸兒擠出一絲勉強還算自然的笑
容,怎麼,不是想知道我和她分手的原因嗎?這次卻是她沒有轉頭向我,只說了一句,
不想。我苦笑了一聲,不想也好,其實就是你想知道我也說不出的。芸兒這才驚訝的轉
過頭來,怎麼會這樣的?我搖搖頭,平靜地說,在99年元旦的夜裡,她留下了一封莫名
其妙的信,然後我就再也沒有能夠和她聯繫上。事實上,當天夜裡我在她們樓下冒著雪
站了一夜,可她甚至都沒有從窗戶裡看我一眼。芸兒接著問,她現在呢?我笑了笑,不
在了,絕症。芸兒一愣,長長地歎了口氣,過了好久才說,其實你應該為她想想的,也
許她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後不想給你負擔呢?我說,有必要嗎?芸兒很認真地說,會啊,
也許在你看來這個想法很可笑,但是如果她真的喜歡你,只要是她看來對你好的事情她
一定會努力去做的,真的。我沒有說話,芸兒就接著說,我以前就有一個朋友,愛她男
朋友愛得死去活來,但是最後得了白血病,她就狠狠地踹了她的,我問她為什麼
,她說這樣那個男生會在以後的日子裡忘了她,繼續快快樂樂地生活。我笑了笑,輕輕
地搖了搖頭,還是不說話。芸兒見我這樣,也就不說話。直到下課以後,我已經收拾好
書本就要離開時,芸兒才又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問我,她最後那封信都說了些什麼?
我剛想回答,卻不知怎麼就冒出了個惡作劇的想法,大聲說,五個字,我們相愛吧!教
室裡,大家本來都在準備離開,聽到我的話都是一愣,接著就都大笑起來。芸兒立刻就
明白過來,在我肩膀小心地大了一下,說,你好壞啊,不理你了啦!然後就紅著臉笑著
跑開了,留下了笑著的大家和我。我笑啊笑啊,但是其實,那個時候,我實在是想哭,
便扭過了頭去,然後悄悄走開。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獨自去了未名湖邊。剛到燕園時逛未名湖,有老爸老媽陪著;後來
呢,就是她陪著;而現在,我身邊誰也沒有。從許久之前,我就再也不想經過所有曾經
的過往,可是現在又要勉強自己去想起她和所有的一切。我不得不承認芸兒的話實在是
很讓我震撼,雖然曾經也有人那麼說過一些類似的話。但是,芸兒的話讓我決定要好好
想想,好好地想想。
其實所有的一切依然是那麼清晰,我始終也都沒有能夠忘記什麼。如果說故意想忘記些
什麼的話,可能是因為她的絕情,而現在也許還多著個尷尬的芸兒。當然,想到芸兒,
我就更加要承認,無論是什麼原因,如果她是在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之後才斷然離開我的
話,那麼這種離開對於我來說都一定是莫大的恩賜。因為,雖然她的生命就像是花瓣上
的朝露一樣在離開我之後就匆忙地消逝了,而我卻依然在幾許遺憾和感慨裡還算是快樂
地生活著。可是,她知道自己的病嗎?秋意正濃得很,未名湖畔的葉子在蕭瑟的秋風裡
飄落著,飛舞著,跳脫著,似乎想要帶走些什麼,可是又似乎什麼也帶不走。我就在這
風這夜裡默默地回憶著所有的如煙往事。我曾經寫過日記的,可是裡一定沒有任何
的痕跡;而她的每一句話似乎也都和自己的身體毫不相干。別想了,我對自己說,因為
在湖畔的寒風裡我忽然覺得有一些恐懼。那個元旦的夜晚,我在她們樓下冒著風雪的時
候,心裡的苦依然刻骨銘心;但是如果我錯怪了她,她的苦又會是怎麼樣的呢?我的確
怕了。既然找不到證據,就別找了吧,我對自己又一次說。於是,這個念頭在又一個不
眠之夜裡就漸漸地隨著夜風飄遠了。
芸兒當然沒有真的生氣,她的確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但是,我還是以向她賠罪的
名義在週末請她吃了一頓飯,又一起去大講堂看了一場電影。開始,弟兄們聽說我要請
她吃飯,就笑著說,要追女孩子也別用這麼老套的辦法嗎,不如認她做小妹子嘍。我笑
了笑,什麼也沒有說,我對芸兒究竟是什麼感覺其實我也說不清楚。影片結束時已經是
很晚了,然後我說,送你回去吧。她搖了搖頭,看著我,甜甜地笑著說,我們去未名湖
邊走走吧。我沒有說話,只盯著她看,然後突然就笑了。她有些慌,說,你這麼怪怪地
看著人家做什麼?我於是就不笑了,突然就拉起了她的手,把她擁到懷裡,說了一句,
走吧。
終究是北方的秋天,離開上一次來湖邊只是隔了一兩場秋雨而已,卻已經冷了許多
。可是未名湖邊那許許多多的垂柳都還沒有凋殘。秋的蕭瑟於是也就不再那麼淒厲,更
何況抬起頭就可以見到明亮的天空,就因為外面不夜的燈火。我就和芸兒坐在湖邊的長
椅上。一陣風吹過,她哆嗦了一下,我就問,冷嗎?她搖了搖頭,歎了口氣,然後像是
自言自語一樣喃喃地說,咱們就永遠坐在這裡該有多好啊。我笑了笑說,真傻。然後我
們就不說話,靜靜地坐在那兒。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我似乎想了好多好多,卻又似乎什
麼也沒有想。反正,過了好久好久之後,我就突然冒出了一句,我和她也來過這兒的。
芸兒似乎哦了一聲,似乎沒有什麼別的反應,但是我分明覺得她握著我的手動了一下。
又過了一陣子,芸兒說,風好涼,我們回去吧。
以後的好一陣子,芸兒再也沒有和我那麼親密,我也沒有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告訴宿舍裡
的弟兄們我知道他們一定會罵我笨,連哄女孩子都不會。反正有的是事情要做,偶爾騙
騙自己,大約什麼事情都可以忘掉,更何況芸兒也沒有對我不理不睬嗎。
西元1999年12月31日,也就是世紀末的最後一天吧,冷冷清清的宿舍裡就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他們五個都去陪老婆了。聽聽歌,玩玩《三國Ⅶ》,總還是覺得無聊,時間就像
是被砍斷了四隻腳的老烏龜,怎麼也走不動似的。好容易捱到晚上十點來鐘,三角地那
兒的歌聲笑聲喝彩聲就絡繹不絕地響了起來。可是我實在是沒有什麼興趣,尤其對於太
熱鬧或者是太冷清的地方。可是總要找些什麼事情來做吧,我歎了口氣,就決定收拾一
下屋子。床上的收拾好了就收拾床下的,床下的收拾好了之後還有桌子,然後還有書架
,還有抽屜。歎了口氣,打開床前的旅行箱,原來裡面裝的是羽絨服,該穿了吧。拿出
來拍一下口袋,居然有一封信,原來是她給我的最後的文字。還有不到一個小時就要走
進新千年了,該忘的就要忘了,趕快回頭看看吧,也許以後就再也沒有這樣的心情了,
我對自己如是說。於是懷著一種幾乎是懷舊的心情,我又一次小心地打開了那封信。很
簡短的一封信,簡潔得一如她的性格。
“已經是一月份了,你見到了嗎,未名湖畔的垂柳都已經凋零不堪了,這個逝去的秋天
再也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以後,再也別來找我了,好嗎?祝你一生快樂幸福。”
我於是又沉默了一陣子,然後笑著對自己說,再過一會兒,那就是一千年以前的事情了
。然後就聽到電話吵了起來,原來是芸兒。她要我到樓下的信箱裡去取信,然後就掛了
電話。我抱著電話至少發了三秒鐘的呆,這才感歎出一句,千禧新新人類!
信自然是很快就取回來了,封口處的膠水似乎還濕著。我有一種預感,我正在說的這個
故事就快要結束了。但是我還是不明白她要弄什麼玄虛,居然在這個時候來開這種玩笑
,有什麼在電話裡說不就結了嗎?信居然也很簡短。
“梅川,我喜歡你。我說過,我相信緣,不相信份。我不會像我以前的那個朋友丁丁一
樣,把所有的真心真意都埋在心底,然後獨自傷心。如果你可以全心全意地喜歡我,我
會在三角地的電話亭等你到0:00。芸兒。”
我大腦裡頓時就只剩空白了。我扔下手頭的所有東西,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只看
了一下牆上的大鐘,還有十來分鐘。我就像是所有經典的愛情故事裡的主人公一樣,毫
不猶豫地沖向三角地,什麼也不想,在擁擠的人群中狂奔,只在這世紀末的最後時刻為
自己浪漫的故事而打拼。越是靠近三角地,人也就越多。大講堂前面居然還臨時搭
了個舞臺,台下還有一口大鐘,很有意思。我當然是不在乎它是否有意思;我要找的不
是它。終於,我看到了芸兒。她就站在路的對面,也正在笑著看著我,一身潔白的衣服
,長髮在風中輕輕的飄動著,眼裡滿漾著笑意。我想走過去,可是路上都是人,而且芸
兒也示意我不用費力過去,於是我就大口地喘著氣,很狼狽的扶著腰,也笑著,全然看
不到來來往往的人,眼裡只有她,我的芸兒。然後,老校長就開始撞鐘了。
“鐺——”“十!——”
成千上萬的人都忽然間安靜下來了,很整齊地喊了起來。芸兒只是笑著,似乎這個世界
只剩下了她和我。我忽然覺得很溫暖,因為終於有一個女孩子可以全心全意地喜歡我,
真心真意的那種。而且,我也是同樣地喜歡著她。這應該是很的事情了吧。
“鐺——”“九!——”
他們都說愛情只有兩種結局,一就是徹底的散,再就是完全的聚,簡單到不能更簡單。
對於曾經的她,也許我的確是徹底的散了;而對於芸兒,除了愛,還能有些別的什麼?
…… ……
“鐺——”“三!——”
我終於有些清醒了。就快要過千年了,就快要告別單身了,對著芸兒的笑容,相識時的
情景也在不經意間浮現,而以往的一切也都在電光火石間從心裡掠過。
“鐺——”“二!——”
未名湖畔的柳樹已經凋零不堪了……再也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我以前的那個朋友
丁丁……以後再也別來找我了……把所有的真心真意都埋進心裡……我是數學系的……
“鐺——”“一!——”
我終於知道原來許多故事的結局都是有可能在最後一秒發生不可思議的變化的了。我說
的這個故事也不例外,雖然在倒數第二秒之前我根本就沒有預見到這種可能性的存在。
“鐺——”
世紀末的鐘聲終於在一千年的漫長等待後敲響了,大家都在歡呼著,雀躍著,釋放著所
有青春的激情和感動。而我卻狂奔在不知會通向哪兒的路上,也顧不得去多想離開時芸
兒那張流著淚的美麗臉龐。那已經不再重要了,我癱在自己的床上對自己說。
元旦之後的英語課我都沒有上,反正也沒有幾節了;他們說芸兒也沒有去上。四級考試
我和她也不在一個考場,於是也就錯過了那個學期最後一次見面的機會。等到再次見到
她,已經到了大三的上半年,也就是不久之前我剛過完二十歲生日的一天。還像是一年
前初次見到她的那個秋天一樣,天很藍,雲很白,秋風下的落葉也很瀟灑,只是芸兒的
身邊已經多了一個英俊高挑的男生。我不由地一陣失落,依舊是穿著自己的破襪子,踩
著比原先又舊了許多的單車,從短髮的她的身邊悄然經過。我沒有回頭,她應該也沒有
。多好的一個女孩子啊,我忽然就笑了。
後來,終於有個朋友問了我一次,你究竟為什麼在最後又放棄了芸兒呢?我笑了笑,說
,其實也沒什麼的,然後就轉過身去,差點兒流下淚來。其實,答案很簡單,卻是我和
芸兒都不曾想到過的。我曾經的那個讓我刻骨銘心的戀人有一個和她一樣美麗的名字叫
做汀芷,而她數學系的同學們則給了她一個更加好聽的名字叫做——丁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