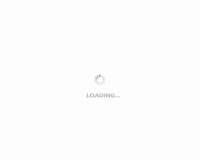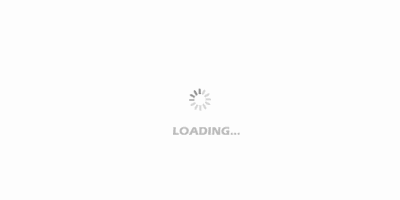(一)
是從誰開始呢,我發現自己已經可以毫不費力地說出“我愛你”了。其時周圍常常有音樂,有很好的燈光,天時地利人和一樣不少。於是總有人會被感動,要麼是說的,要麼是聽的,哪怕只是片刻包含欺騙性的感動。畢竟,只說過一次“我愛你”的人,並不見得比說過一千次的人高尚;而即使聽過一千次虛假的“我愛你”,我們還是希望第一千零一次是真的。
(二)
有一天,我和現男友Mark逛街,遇到了前度男友之一的小凡,大家就坐到咖啡館裡去歇腳。我和Mark並排坐著,小凡坐在對面,旁邊是他現在的那個她。Mark用胳膊環著我的肩,
我們細細碎碎地聊著天,甚至不知誰還提議要打兩把拖拉機。兩邊的兩個不明就裡,中間的一對暗懷心機。這個組合就像基因的排列組合遊戲,有四種各不相同的“我愛你”在裡面偷偷過著招。這感覺,舊愛新歡時光惝恍,奇妙但並不美好。
從咖啡館出來,我一直默不作聲。Mark即將出國,在一邊自顧自地興致勃勃描述著他和我的未來。他說美國的有錢人都住木頭房子,窮人才住Apartment,總有一天,我要讓你住上木頭房子。我很乾澀地笑笑,說,好啊。那一刻我突然發現自己竟然像在聽笑話一樣聽著Mark描述的一切。打心眼裡,我對MARK感覺不過了了,不相信自己會住進他的木頭房子,也覺得沒有什麼力量足夠讓我和這個男人很老派很專情地千山萬水永不分離。
(三)
和老王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家粵菜館。
老王戴一副沒有鑲邊的眼鏡,每隔兩分鐘扶一下眼鏡架,他手指細長骨節清朗,這個習慣性的身體語言因而就帶上了種知識份子式的性☆禁☆感。
老王端起茶壺,為我添茶。我禮節性地用手指敲著桌面。我那天穿了件小素花短旗袍,是不動聲色裡藏了千言萬語的款式。聖羅蘭唇膏正在唇上一點點殷開,白瓷花杯上的一圈紅漬是一個羞澀而鮮潤的表情。
我把小茶杯攥在手裡,趁老王不注意用餐巾紙擦掉了那圈紅漬。
一個朋友介紹老王找到我,讓我幫忙做個設計,我很不客氣地開出了價。老王並未表示異議,
堂中彌漫著粵式小曲,女藝人甜絲絲的聲音在我們中間纏鬥糾結,給所有的對話都鑲上了一重曖昧的花邊。這樣的兩個人,大概怎麼看去都不像平白無故,倒像是藏著千絲萬縷的過去和將來似的。
(四)
Mark正忙著辦出國的事,每次見面都是欣欣然的樣子,再向我描述一番我和他的美好前景,他的描述越來越細節化,甚至很無厘頭得具體到了沙發靠墊的顏色和餐桌的質地。他說得越煞有其事就越讓我感到和自己無關。
一天深夜,Mark跑到我這裡,一進門就抱緊了我,然後大聲說:“我愛你,我要讓你住上木頭房子。”他身上有非常濃重的酒精味道,壓迫得我喘不過氣。我從他的擁抱中掙脫出來,
(五)
粵菜館之後,我和老王有了一些一起吃飯的機會。有時是他請我幫忙做設計,有時好象就是為了吃飯而吃飯。他坐在我對面,在語言和表情上都很節制。他已經過了會努力描述什麼的年齡,也很少使用幅度大的手勢。
我給老王講一些小笑話,是從網上看來的。他會很放鬆地笑,但我覺得他的笑並非發自內心,
吃完飯老王一般會開車送我回家,在車上我開玩笑說現在是我的點歌時間。老王就問小姐你想點什麼歌,我會說出一串歌名。老王的車上有一大堆CD,但他 和我有截然不同的愛好。老王喜歡三套車,而我卻喜歡BBKING那種鈍而滄桑的外國老男人嗓音。老王心情好的時候,會主動地唱上兩句,是不太地道的男低音。我說,嘿,其實你可以改行唱爵士呢。
我偶爾也唱,是潘越雲蔡琴那個路子的怨婦歌。有次我唱潘越雲的《你是我一輩子的愛》,唱到“你總是那個樣,一副男人該有的狂,你從來不問我你今天吃飯了嗎?”老王嘣不住笑了,他摸了摸我的頭髮,說,我可是經常問你“你今天吃飯了嗎”。
(六)
Mark坐著飛機奔赴美洲大陸的那天,我躲在家裡看長篇日劇。日劇裡的男人和女人愛得昏天黑地死去活來,我的心裡像是裂開了一個巨大的空洞……我並不為Mark的離去而痛苦,關於愛情的所有回憶都因為沒有痛感而有氣無力,所有感覺都因為失去重量而似是而非。在這一天,我終於明白,一直以來,我最大的痛苦,其實就是失去了痛苦的能力。
晚上我約了老王在熟諳的小茶館裡。我不停地喝苦丁茶,嗑瓜子。然後要老王開車送我回家。在車上,老王問小姐你想點什麼歌。我懶懶地靠在座位上說什麼都不想點。老王問出什麼事了。我終於開始暴發式的痛哭流涕,我說我覺得自己好象從來沒有真正愛過誰,誰也沒有真正愛過我。
這天老王第一次進入了我的房間,這是一座高層住宅的七樓。已近深夜,門外有警衛用對講機小聲說話的聲音,窗外的城市是一副疲倦睡去的模樣。
老王坐在我旁邊,說我等你睡著就走。我小聲說:抱抱我。老王猶豫了一下,終於伸出雙臂抱住我,在他的擁抱中,我還是感到了他刻意製造的最後一點距離。老王用雙手在我背後輕輕拍打了一下,然後鬆開我,說,睡吧。我想這已是他的極限,我點點頭,閉上了眼睛。
老王離開的時候,我並沒有真正睡著。我聽到他替我關了燈,然後輕輕退出去,把門帶上。
(七)
我曾經問老王在我這樣的年紀他在做什麼?他說,那時剛畢業,分在機關裡,白天喝茶看報紙,晚上在小酒館裡和朋友談人生談理想。我苦笑了一下說,你們真幸福,我卻沒過上一天理想主義的日子,自從畢業後就好象被扔到了滾滾紅塵裡,一直為所謂生計和瞎忙活。老王點點頭,說現在的小孩子是不容易啊。我說,我們會比你們更早地體驗到累和絕望。
這天老王帶我來到一所大學附近殘敗不堪的小酒館,那裡幾乎所有的餐具都帶著小缺口,燈光白刷刷得亮著,一點遮攔和矯飾都沒有,在這樣的燈光下,兩個人看起來都顯得有點無精打采。老王說這裡就是以前我們談人生談理想的地方。
在這個殘存著老王青春印跡的小酒館裡,我問老王,你的理想實現了嗎?老王說,應該說是實現了吧。只是實現了從前的理想,又有了現在的理想,慢慢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說完,他握住我的手,說,我老說你是傻孩子,其實自己是個傻老頭。
我看著老王,他兩邊的鬢角已經開始花白,一個中年男人的疲倦和衰老忽然全湧到了臉上。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他為什麼願意跟我一起消磨時間,我們都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我們一直在追逐,他在事業上,我在感情上。我們都好象得到了很多,但其實又好象什麼都沒得到。在這個城市裡,我們是兩個同樣失重的人。
那天是老王第二次進入我的房間。隔著長長的歲月和彼此不知道的經歷,我們緊緊相擁在一起。有一個瞬間我很想對老王說“我愛你”,但最終沒能說出口。在老王面前,“我愛你”終於難產和早夭了。
(八)
很久以後,我在休斯頓街頭閒逛,看到了一個男人的側影。我正在試穿一雙涼鞋,照鏡子時我看到他從門前經過。
我慌忙換了鞋追出門。那個男人高而瘦,穿一件灰色的襯衫,水洗布褲子。我尾隨著他走了大約一百米,在這一百米的長度裡,我的心一直在狂跳。他忽然回過頭來,張望什麼的樣子,給了我一個很清楚的正臉。
他不是老王,只是略略有點像。
我已經在老王面前消失很久了,從那個我沒能說出“我愛你”的夜裡。我心中關於老王最後的印象,是那天深夜我送他出門。他向我招了一下手。他穿著一件灰色的襯衫,高而瘦,隔開一段距離,隔著夜色,他身上的那種憔悴和無可奈何讓人疼痛。
我一直慶倖自己沒有對老王說“我愛你”,也許正因此,我的心中才終於留住了那種久違的痛感。
(九)
現在我要結婚了,要嫁的人,是當年那個喋喋不休向我描述沙發靠墊顏色和餐桌質地的Mark。
我不停地喝苦丁茶,嗑瓜子。然後要老王開車送我回家。在車上,老王問小姐你想點什麼歌。我懶懶地靠在座位上說什麼都不想點。老王問出什麼事了。我終於開始暴發式的痛哭流涕,我說我覺得自己好象從來沒有真正愛過誰,誰也沒有真正愛過我。
這天老王第一次進入了我的房間,這是一座高層住宅的七樓。已近深夜,門外有警衛用對講機小聲說話的聲音,窗外的城市是一副疲倦睡去的模樣。
老王坐在我旁邊,說我等你睡著就走。我小聲說:抱抱我。老王猶豫了一下,終於伸出雙臂抱住我,在他的擁抱中,我還是感到了他刻意製造的最後一點距離。老王用雙手在我背後輕輕拍打了一下,然後鬆開我,說,睡吧。我想這已是他的極限,我點點頭,閉上了眼睛。
老王離開的時候,我並沒有真正睡著。我聽到他替我關了燈,然後輕輕退出去,把門帶上。
(七)
我曾經問老王在我這樣的年紀他在做什麼?他說,那時剛畢業,分在機關裡,白天喝茶看報紙,晚上在小酒館裡和朋友談人生談理想。我苦笑了一下說,你們真幸福,我卻沒過上一天理想主義的日子,自從畢業後就好象被扔到了滾滾紅塵裡,一直為所謂生計和瞎忙活。老王點點頭,說現在的小孩子是不容易啊。我說,我們會比你們更早地體驗到累和絕望。
這天老王帶我來到一所大學附近殘敗不堪的小酒館,那裡幾乎所有的餐具都帶著小缺口,燈光白刷刷得亮著,一點遮攔和矯飾都沒有,在這樣的燈光下,兩個人看起來都顯得有點無精打采。老王說這裡就是以前我們談人生談理想的地方。
在這個殘存著老王青春印跡的小酒館裡,我問老王,你的理想實現了嗎?老王說,應該說是實現了吧。只是實現了從前的理想,又有了現在的理想,慢慢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了。說完,他握住我的手,說,我老說你是傻孩子,其實自己是個傻老頭。
我看著老王,他兩邊的鬢角已經開始花白,一個中年男人的疲倦和衰老忽然全湧到了臉上。一瞬間我突然明白他為什麼願意跟我一起消磨時間,我們都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人,我們一直在追逐,他在事業上,我在感情上。我們都好象得到了很多,但其實又好象什麼都沒得到。在這個城市裡,我們是兩個同樣失重的人。
那天是老王第二次進入我的房間。隔著長長的歲月和彼此不知道的經歷,我們緊緊相擁在一起。有一個瞬間我很想對老王說“我愛你”,但最終沒能說出口。在老王面前,“我愛你”終於難產和早夭了。
(八)
很久以後,我在休斯頓街頭閒逛,看到了一個男人的側影。我正在試穿一雙涼鞋,照鏡子時我看到他從門前經過。
我慌忙換了鞋追出門。那個男人高而瘦,穿一件灰色的襯衫,水洗布褲子。我尾隨著他走了大約一百米,在這一百米的長度裡,我的心一直在狂跳。他忽然回過頭來,張望什麼的樣子,給了我一個很清楚的正臉。
他不是老王,只是略略有點像。
我已經在老王面前消失很久了,從那個我沒能說出“我愛你”的夜裡。我心中關於老王最後的印象,是那天深夜我送他出門。他向我招了一下手。他穿著一件灰色的襯衫,高而瘦,隔開一段距離,隔著夜色,他身上的那種憔悴和無可奈何讓人疼痛。
我一直慶倖自己沒有對老王說“我愛你”,也許正因此,我的心中才終於留住了那種久違的痛感。
(九)
現在我要結婚了,要嫁的人,是當年那個喋喋不休向我描述沙發靠墊顏色和餐桌質地的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