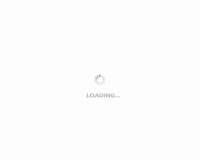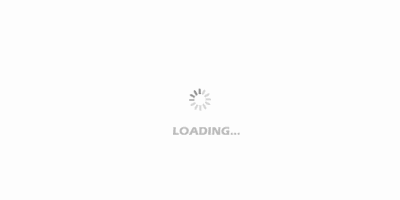我們的內心,隔著時空,有著這樣隱秘的呼應。
第一次見他,他就是那樣落落寡歡的樣子
那是個我不常去的聚會,也是他的。眾人紮堆,遠遠就看見他,一個人,坐在那個角落。
現代社交,說落落寡歡簡直就是犯酸。裝酷還勉強說得過去,但他那種表情,卻不是為了吸引什麼人。而越是如此,越是吸引——就這一點而言,人又是犯賤的。
我走過去,問他:“有煙嗎?”他便遞過來一支。是我常抽的中南海。和中南海一起遞過來的,還有打火機。也沒多說,抽完煙再問他:“出去走走?”他說好。
屋子外面有個小小的水池。“你做什麼?”我問他。
他沒有不高興。更沒料到他說了一句:“哪兒都一樣。沒什麼。”
女伴在叫我,便要走開。走時回了一回頭,他已轉身,對著水池,背對我。當時有個感覺,我們,一定會再見的。
很快就再見了,在我們公司的工程部。
那天下班在電梯裡,電梯裡人多,我們之間隔著兩三個人,他在一角,我在一角。他於我之前走出,就在那個大門門口,他站住了,等我。
我上去了,也沒多說什麼,“去吃飯?”他說好。我算是地頭蛇,他便跟著。
坐在靠窗的位子,太陽明晃晃地,照著他和我。點菜時我問他:“能吃辣嗎?”我問的時候,
那一刻的全部感覺便是默契。像極茶杯上的兩行字:與君初相識,似是故人來。
真是緣分。我不嫌他悶,他也不嫌我咄咄逼人。N頓飯吃下來,在公司已被傳作情侶。
一天他送我回家,我問他:“都說我凶,為什麼和我在一起?”
他說:“不知道為什麼,只覺得你親切。”
呵,親切。這個答案讓人滿意。那個樓梯口四顧無人。我突然停住,踮起腳尖,攀附他的高度,吻了他。
我們不久便住到一起。做飯、洗衣。不由得想起初戀,那個大學的學長說:“我喜歡的女孩子,不是你這樣的。”那時的我。比現在更囂張,自恃才氣。而彼時他坐在沙發的另一端,捧著我的腳,在他懷裡細細撫看。他說過,腳趾都那麼漂亮——真的不相信可以如此被寵愛。
有一回我出差一星期,和同行女子住在標間。晚晚他都打電話來,只說:“今天一天,都沒聽見你的聲音。”同行嘖嘖,直說羡慕。
那時真是幸福,誰說學理工的男子不解溫柔?說那句話時,他像進過瓊瑤培訓班似的。
春節我父母過來。那個春節我媽媽果然視他如子,給他夾一塊魚,直看著他吃完,才停了炯炯注視。媽說:“這孩子很好,你要珍惜。”
自然,我自然珍惜。因為他的包容我們從無爭吵,直到我接到那個電話。聽見我的聲音那頭非常遲疑,年老婦人的聲音,一遲疑便顯怯意。“你是——小峰的嗎?”
當時便覺有異,接住話頭,不肯放手。而那聲音,竟然來自他媽媽,他口中早已去世的媽媽。
約在某處,我見了他媽媽。
那一刻我眼中有淚。她的小峰我的阿狗,是的,我一直這樣叫他。那天我回去,他正在廚房做飯,我沖進去便抱住他。他舉起油膩的雙手,說:“好了好了,別搗亂啊。”
我說為什麼不告訴我,我說你媽媽——我帶回了他媽媽。永遠忘不了他看見她時的表情,那麼斯文的他,竟然狠狠地說了一句:“你是誰?我認識你嗎?”
我勸他,他便沉默。如石頭。我說:“你看她這麼老了。”
他說:“你不會明白的。”我說我明白,他說:“你不會明白的。
同一句話重複三次,忽然他就暴怒。不摔東西更不打人,他坐著,緊緊的低頭緊緊的低頭,我看見那一道道的青筋,我想要去撫摸他,他便死死抓住我的手。手被他握得痛了。
他始終不肯認他媽媽。我們的爭吵便開始。如他所言我只看到現在的她那麼卑微,慈眉善目,怯怯如丐。我不知道她當初丟下他時的狠心。一個月後她傷心而去。送他媽媽上飛機,回去時他還是在做飯。第一次,我也沉默如石頭。
我以為我們之間過一陣子就會好。就像我說的,她畢竟是他媽媽。媽媽這個詞有多麼溫暖,傷有多深愛便有多深。
在他還沒有愛上我的時候,我愛上過另一個人。
可是我遇到另一個人了。留在記憶裡揮之不去的,大學的學長,那高傲的男孩子說:“我喜歡的女孩子,
閱過了世事,那個叫浩的男人來找我,對我說,這麼多年,身邊的女孩子來了又去,這才發現,我從來沒有離開過他———他的說得比我的阿狗好,他的吻也比我的阿狗有技巧———推開他我才悔悟,逃開他我在反省,我為什麼,拒絕不了他。我想那只是因為女人對於她們的初戀都難以割捨,我想那只是一時的意亂情迷。可是只要他來找我,我便拒絕不了他。於是那樣一天,我和浩在車內擁吻,我的阿狗看見了。
那個晚上,我們都沉默得可怕。坐在沙發上對峙半晌,我起來去接一杯水,他突然便拉住我,他說:“你也要丟下我嗎?”
他沒有等我回答。他將我的手捏出一道青紫的痕,他將我的嘴唇咬破———我大叫著:“那你要怎樣?殺了我嗎?”
我奪門而出,被他拽回去。他拽得那麼粗暴,我也開始暴怒了,我說:“姓程的,乾脆我們說清楚!”我那麼兇悍,他也不復平日退讓,這才發現他其實是很精明的,那個關口他只問我:“你愛他多還是愛我多?”
我說:“你不知道嗎?你不知道就不要問我!”
我算是給了他一個答覆。可是我錯了,他要的不是我的答覆,他真正希望的是我將他的問題全盤否定,他要我的全部。我是他惟一的愛人。這麼多年,他身邊惟一的女子。可是這又怎樣呢?我怎麼知道我會在25歲的時候遇見這樣一個完美的愛人,27年來留著空白只等著我。
那個晚上我吵著,暴怒著,和他糾纏。快12點的時候,他竟然問我餓了沒有,要不要吃飯?我看著這個分明憤怒到極點的男人,第一次覺得了陌生,我說程峰,我真的瞭解你嗎?
他抓著我,說明天就去公證結婚。我說我不會去。
其實所謂的默契,一定有它的理由,一定有許多我們沒有想到的秘密。
他永遠不會知道我其實是我的養女,25年前他們自孤兒院把我抱來,我的身世便是某天清晨孤兒院門前一隻盛有女嬰的竹籃———連我的養母都不知道我在15歲那年聽到他們的談話明白這一切,我把這秘密讓自己一個人獨享。我告訴自己我就是他們的親生女兒,他們就是我的親生。
所以我那麼驕傲那麼兇悍,所以我讓自己活得燦爛如花。縱然我把一切都往好處去想,那只盛有女嬰的竹籃,是我的暗湧。
那夜我終於睡著。我又在半夜醒來,看見他灼灼的眼。忽然我就哭了,抱住他說你不要這樣好不好?我丟下他他便再入深淵,而我也一樣。我知道二十年前的絕望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他,它也在他心裡陰沉起伏,也是一場暗湧。
我們的內心就這樣隔著時空,有著隱秘的呼應。
所以,我們相愛。
所以,我聽他的話。第二天,和他去公證結婚了。
我奪門而出,被他拽回去。他拽得那麼粗暴,我也開始暴怒了,我說:“姓程的,乾脆我們說清楚!”我那麼兇悍,他也不復平日退讓,這才發現他其實是很精明的,那個關口他只問我:“你愛他多還是愛我多?”
我說:“你不知道嗎?你不知道就不要問我!”
我算是給了他一個答覆。可是我錯了,他要的不是我的答覆,他真正希望的是我將他的問題全盤否定,他要我的全部。我是他惟一的愛人。這麼多年,他身邊惟一的女子。可是這又怎樣呢?我怎麼知道我會在25歲的時候遇見這樣一個完美的愛人,27年來留著空白只等著我。
那個晚上我吵著,暴怒著,和他糾纏。快12點的時候,他竟然問我餓了沒有,要不要吃飯?我看著這個分明憤怒到極點的男人,第一次覺得了陌生,我說程峰,我真的瞭解你嗎?
他抓著我,說明天就去公證結婚。我說我不會去。
其實所謂的默契,一定有它的理由,一定有許多我們沒有想到的秘密。
他永遠不會知道我其實是我的養女,25年前他們自孤兒院把我抱來,我的身世便是某天清晨孤兒院門前一隻盛有女嬰的竹籃———連我的養母都不知道我在15歲那年聽到他們的談話明白這一切,我把這秘密讓自己一個人獨享。我告訴自己我就是他們的親生女兒,他們就是我的親生。
所以我那麼驕傲那麼兇悍,所以我讓自己活得燦爛如花。縱然我把一切都往好處去想,那只盛有女嬰的竹籃,是我的暗湧。
那夜我終於睡著。我又在半夜醒來,看見他灼灼的眼。忽然我就哭了,抱住他說你不要這樣好不好?我丟下他他便再入深淵,而我也一樣。我知道二十年前的絕望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他,它也在他心裡陰沉起伏,也是一場暗湧。
我們的內心就這樣隔著時空,有著隱秘的呼應。
所以,我們相愛。
所以,我聽他的話。第二天,和他去公證結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