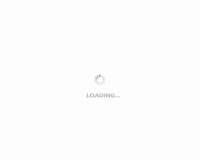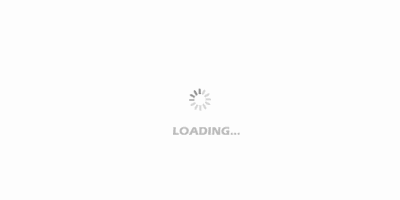遇上瞿煒那年秋天,我在一家合資企業做文員。無關風月情愛,生活平靜得像一泓湖水。
在朋友的生日派對上,有一位風度翩翩的男子,一曲《相思風雨中》讓全場的人為之喝彩。
他就是瞿煒,尋著他深情的歌聲望去,我們四目相對。他用那種穿透心靈的眼神看我,像是凝視深愛了多年的戀人,而此時,我們還沒談上3句話。
我開始覺得,我會和這個30歲的男人糾纏不清。
他從我的朋友那知道了我的e-mail,發來了他的心路歷程,他是一所中學的領導,卻夢想著開一間酒吧,曾經深深地愛過一次,無疾而終。我相信了他。
記得有一次到郊外燒烤,碳火灼傷了我的手指。瞿煒搶過我灼紅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吹,他專注而心疼的樣子讓我忽然有一些感動,在這個異鄉的郊外,他的樣子深深打動了我。眼裡有淚在閃,不是因為疼,而是心底泛起了莫名的委屈,讓我倍感孤獨。我的手沒抽出來,在他的掌心裡,暖暖的、細細的汗水溢了出來。
從那一天開始,上班時的心總是浮著的,就像幸福就在不遠的地方飄著,然後盯著話機出神,手指在起起落落間總想撥通他的聲音。終於撥通他的電話,我輕輕說:“嗨,是我,木子。”他的聲音很快樂,說:“我正想找你,今晚我家有派對,你也來,行嗎?”“我不知道怎麼去。”瞿煒說你在某個車站旁邊等我。
他牽著我的手走在城市的街上,路上的景致都沒有入眼,原來,愛情可以讓人忽略身邊的很多風景。派對有點冷清,現在的都市人已經不太有人熱衷於此,曲終人散,瞿煒送我回家,走在路上他忽然問:“木子,你說還會不會有人愛我?”我說:“這要看你自己的造化。”我本想說會,但這個答案過於明確,現在我不想說。
站在冷清的月光下,身後是一片低矮的棚戶區,在高樓大廈之間顯得有點卑微。“轉來轉去居然沒走出去?”我問他。瞿煒不答,笑著說:“以前我很怕別人到我家玩,我怕他們嘲笑我住在貧民區裡。”我笑:貧民區有什麼不好嗎?瞿煒忽然拉起我的手,
那一晚,慢慢地,我貼在他懷裡,跳一支沒有規則沒有終了的舞。當一切在昏黃的燈下結束時,忽然想起,還沒來得及被承諾。
去瞿煒家的路,即使去過多次,我照樣記不住,我依舊會迷失在迷宮樣的胡同裡,每次都要瞿煒一路接去,這樣的,反而溫暖了許多。看到他,我的心就會安然,
某一天,瞿煒說:“木子,我想開間酒吧,支持我嗎?”這是他一直的夢想。我說:“只要是你喜歡的,我都支持。”
瞿煒停薪留職,開始專心經營他的酒吧。酒吧的生意很好,瞿煒的臉也很陽光,下班後,我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去酒吧找他,看他坐在掛滿高腳杯的吧台裡和每一個湊近吧台的人說說笑笑,很休閒的臉和酒吧的氣氛相符。很快,在酒吧,我感受到一雙針芒樣挑來刺去的眼睛,來自一個叫小紅的酒吧小姐,她的臉上總掛著玩世不恭的不屑,一雙歷經風塵的媚眼,染著火一樣紅的頭髮。而我的臉總是素面朝天,我的發總是直直地垂下來,我喜歡自己本來的樣子。當我坐在瞿煒身旁,看他調製各種看起來美麗無比的酒水,
每一次,與小紅的沉默對峙之後,我就開始嚮往瞿煒的承諾,與小紅這樣的女孩競爭,我沒有信心,那樣的妖冶,是男人都動心的。
一個夜晚,我問瞿煒:“你愛我嗎?”他看著我,手裡的煙灰一點點掉下來,他坐在沙發上,看我的臉。我又問:“你愛不愛我?”“愛難道需要說出來嗎?你知道我不善於表達。”我只好把這樣的話當作承諾。大概這也算愛情的一種形式吧。
在辦公室,除了做每天必須的工作,其餘的時間幾乎全部用來思念瞿煒,沒有具體細節,有關他的細膩、還有他生活的調子,
除了星期天,我都是在夜幕剛剛開始降臨的時候,手裡拎著瞿煒喜愛的食物,在天色微藍的時刻帶著一份對的信任,悄然無聲地來到他的酒吧。
那個黃昏,去得有點早,妖妖的小紅遠遠地看著我進門,然後對貓在吧台裡找東西的瞿煒大聲喊:“瞿煒,我愛你!”瞿煒的聲音從吧台裡蹦出來,像冰做的針,散漫著刺向我:“我也愛你,小紅妖精。”
那句話,我等了很久,瞿煒沒有說,卻在這樣一個場合,這樣一個女孩子面前,他說出來,象呼吸一口並不怎麼特別的空氣。我的心,在碎落,它們在憂傷的懷舊老歌裡一點點飄遠。我愛過,卻沒有承諾。
我敲敲吧台,瞿煒鑽出來,看我沒有血色的臉龐,看得意的小紅妖精,很快躲開我的視線,悄悄地說:“我們只是在開玩笑。”“這樣的玩笑怎麼不對我開?”我大聲吼道。眼淚一顆一顆落下來,滴在手裡的便當盒上,又一滴一滴濺碎,打在手上,它們冰涼。
瞿煒拿出紙巾,給我拭淚,眼淚飛快地流,擦不及,紙巾沾在臉上,像他每一次的體貼,總來得及時,這樣溫柔,而在此刻,卻讓我心碎。瞿煒拉著我到他窄小的辦公室,不停地為我擦淚是他惟一能做的事情。
“你知道小紅這樣的女孩子,說愛比喝白水都要輕鬆。”瞿煒說。“那我呢?”“如果對你說了,就是承諾,她可以是玩笑。”“瞿煒,我一直以為你是愛我的。”原來,瞿煒的愛不可以對我承諾,愛情是一種責任,他不想留給我。我不想要這樣的愛情,只想愛一個人,可以讓我的愛在他心裡安家,不再飄泊。
跟瞿煒說再見的時候,是在他又一次和小紅打情罵俏的晚上,他站在酒吧的門口,出奇得平靜,我難以想像,這就是我愛的那個人。
我用自己認為美好的方式活著,用青春的美麗和漫長尋找愛情。
一年後,在一家商場的休息茶室,我看到了小紅,她還是原來的樣子,妖妖冶冶地媚笑。我走過去和她打招呼,她看著我,臉上竟是不曾相識的陌生。我說了些有關瞿煒酒吧的事情,她才顯出恍然的樣子,有點驚訝地說:“你居然還記得瞿煒?我都快忘記他了。”
我笑:“我真的愛過他,所以忘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紅看著我,難道我對他的愛是假的?她從坤包裡抽出一支香煙,“啪”的一聲點上,又斜斜地看著我,一副坦然的樣子。“瞿煒是愛過你,但他不會娶你,因為你沒有社會背景。”我的心,還有一些微微的疼,他以為不說愛我,就會減少傷害。
小紅認真地回憶著,說:“瞿煒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小紅,你離我遠點,即使你是天仙也不行,如果你是市長的女兒,哪怕你瞎了一隻眼、高位截癱,我也會娶你,別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小紅說:“我只是一個媚笑惑人的小女子,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我一個外地分到這個城市的女孩子,除了工作單位幾乎不認識任何人,4年的大學生活,沒有給我任何讓瞿煒愛的資本。愛情于他,原來只是一種交易,是可以改變人生的一個契機。小紅還告訴我,瞿煒現在已經結婚了,他娶了一個天天去他酒吧喝酒的女孩子,她父親是本地富豪。
小紅說了一個媒體上經常看到的名字。我想,他終於可以搬出那片讓他感到羞愧的貧民區了。
某天,我路過本市的一片別墅區,看見遠遠而來的瞿煒,他已經有點發福,步態少了些輕捷。他停下腳步,看著我,無從說起的樣子,顯得很不自然。
半晌,他終於說話:“木子,你過得好嗎?”
我說好,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能不好麼?
我沒問他,幸福於他只是一個名詞,說與不說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木子,你不想問我點什麼?”
我搖搖頭。
我說愛情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我們不同的生活方式,還有對生活不同的理解。我們相互錯過,彼此的影子漂在路上,從沒找到過屬於自己的家園,用不同的方式,走在路上。我們不知道未來,卻執著地做著各自的夢,誰都不願放棄。這就是生活的景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進行方式。看得意的小紅妖精,很快躲開我的視線,悄悄地說:“我們只是在開玩笑。”“這樣的玩笑怎麼不對我開?”我大聲吼道。眼淚一顆一顆落下來,滴在手裡的便當盒上,又一滴一滴濺碎,打在手上,它們冰涼。
瞿煒拿出紙巾,給我拭淚,眼淚飛快地流,擦不及,紙巾沾在臉上,像他每一次的體貼,總來得及時,這樣溫柔,而在此刻,卻讓我心碎。瞿煒拉著我到他窄小的辦公室,不停地為我擦淚是他惟一能做的事情。
“你知道小紅這樣的女孩子,說愛比喝白水都要輕鬆。”瞿煒說。“那我呢?”“如果對你說了,就是承諾,她可以是玩笑。”“瞿煒,我一直以為你是愛我的。”原來,瞿煒的愛不可以對我承諾,愛情是一種責任,他不想留給我。我不想要這樣的愛情,只想愛一個人,可以讓我的愛在他心裡安家,不再飄泊。
跟瞿煒說再見的時候,是在他又一次和小紅打情罵俏的晚上,他站在酒吧的門口,出奇得平靜,我難以想像,這就是我愛的那個人。
我用自己認為美好的方式活著,用青春的美麗和漫長尋找愛情。
一年後,在一家商場的休息茶室,我看到了小紅,她還是原來的樣子,妖妖冶冶地媚笑。我走過去和她打招呼,她看著我,臉上竟是不曾相識的陌生。我說了些有關瞿煒酒吧的事情,她才顯出恍然的樣子,有點驚訝地說:“你居然還記得瞿煒?我都快忘記他了。”
我笑:“我真的愛過他,所以忘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小紅看著我,難道我對他的愛是假的?她從坤包裡抽出一支香煙,“啪”的一聲點上,又斜斜地看著我,一副坦然的樣子。“瞿煒是愛過你,但他不會娶你,因為你沒有社會背景。”我的心,還有一些微微的疼,他以為不說愛我,就會減少傷害。
小紅認真地回憶著,說:“瞿煒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小紅,你離我遠點,即使你是天仙也不行,如果你是市長的女兒,哪怕你瞎了一隻眼、高位截癱,我也會娶你,別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小紅說:“我只是一個媚笑惑人的小女子,你明白嗎?”
我明白了,我一個外地分到這個城市的女孩子,除了工作單位幾乎不認識任何人,4年的大學生活,沒有給我任何讓瞿煒愛的資本。愛情于他,原來只是一種交易,是可以改變人生的一個契機。小紅還告訴我,瞿煒現在已經結婚了,他娶了一個天天去他酒吧喝酒的女孩子,她父親是本地富豪。
小紅說了一個媒體上經常看到的名字。我想,他終於可以搬出那片讓他感到羞愧的貧民區了。
某天,我路過本市的一片別墅區,看見遠遠而來的瞿煒,他已經有點發福,步態少了些輕捷。他停下腳步,看著我,無從說起的樣子,顯得很不自然。
半晌,他終於說話:“木子,你過得好嗎?”
我說好,用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能不好麼?
我沒問他,幸福於他只是一個名詞,說與不說都沒有太大的意義。
“木子,你不想問我點什麼?”
我搖搖頭。
我說愛情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我們不同的生活方式,還有對生活不同的理解。我們相互錯過,彼此的影子漂在路上,從沒找到過屬於自己的家園,用不同的方式,走在路上。我們不知道未來,卻執著地做著各自的夢,誰都不願放棄。這就是生活的景色,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進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