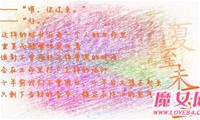《詩經: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注釋:
1:泛泛:船在水蔔行走的樣子。景:同“憬”,遠行的樣子。
2:願: 思念的樣子。言:語氣助詞,沒有實義。
3:中心:心中。養養:憂愁不定的樣子。
4:逝:往。
5:不暇:該不會。
譯文:
兩個孩子乘木舟,順江漂流去遠遊。
時常掛念遠遊子,心中不安無限愁。
兩個孩子乘木舟,順江漂流去遠遊。
時常掛念遠遊子,該不遇上險與禍?
賞析:
母子之情是人世間天然的、最為牢固的血緣紐帶。這一點,只要人類存在一天,大概是不會改變的。
寫人之常情,征夫恨,
人們常說,母愛是無私的。這話一點不假。從十月懷胎,到一朝分娩,到孩子張大成人,到孩子闖蕩社會漂泊天涯,母親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既有肉體的,也有精神的。換個說法,母親是在用她畢生的心血進行創造:創造生命,創造自己的作品。
孩子作為母親創造的作品,雖是另一個存在,另一個生命,卻時刻牽動著創造者心。他的榮辱沉浮,
《詩經:谷風》
習習穀風,以陰以雨。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宴爾新婚,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
宴爾新婚,不我屑以。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泳之遊之。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畜,反以我為仇。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
既生既育,比予於毒。
我有旨蓄,
宴爾新婚,以我禦窮。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
不念昔者,伊餘來塈。
注釋:
1、習習:和暖舒適的樣子。穀風:東風。
2、黽勉:努力,勤奮。
3、葑、菲:蔓菁、蘿蔔一類的菜。
4、不以:不用。下體:根部。
5、德音:指夫妻間的誓言。違:背,背棄。
6、遲遲:緩慢的樣子。
7、中心:心中。違:恨,怨恨。
8、伊:是。邇:近。
9、薄:語氣助詞,沒有實義。畿:門檻。
10、荼:苦菜。
11、薺:芥菜,味甜。
12、宴:樂,安樂。
13、涇:涇水,其水清澈。渭:渭水,其水渾濁。
14、湜湜:水清見底的樣子。沚:止,沉澱。
15、不我屑以:不願意同我親近。
16、梁:河中為捕魚壘成的石堤。
17、發:打開。笱:捕魚的竹籠。
18、躬:自身。閱:容納。
19、遑:空閒。恤:憂,顧念。
20、方:用木筏渡河。舟;用船渡河。
21、喪:災禍。
22、匍匐:爬行。這裡的意思是盡力而為。
23、慉:好,愛。
24、讎:同“仇”。
25、阻:拒絕。
26、賈:賣。不售:賣不掉。
27、育恐:生活在恐懼中。育鞠:生活在貧窮中。
28、顛覆:艱難,患難。
29、毒;害人之物。
30、旨蓄:儲藏的美味蔬菜。
31、洸:粗暴。潰:發怒。
32、既:盡。詒:遺留,留下。肄:辛勞。
23、伊:惟,只有。餘:我。來:語氣助詞,沒有實義。墍:愛。
譯文:
和熙東風輕輕吹,陰雲到來雨淒淒。
同心協力苦相處,不該動輒就發怒。
採摘蔓菁和蘿蔔,怎能拋棄其根部。
相約誓言不能忘,與你相伴直到死。
出門行路慢慢走,心中滿懷怨和愁。
路途不遠不相送,只到門前就止步。
誰說苦菜味道苦,和我相比甜如薺。
你們新婚樂融融,親熱相待如弟兄。
有了渭河涇河渾,涇河停流也會清。
你們新婚樂融融,從此不再親近我。
不要去我魚梁上,不要打開我魚籠。
我身尚且不能安,哪裡還能顧今後。
過河遇到水深處,乘坐竹筏和木舟。
過河遇到水淺處,下水游泳把河渡。
家中東西有與無,盡心盡力去謀求。
親朋鄰里有危難,全力以赴去救助。
你已不會再愛我,反而把我當敵仇。
你已拒絕我善意,就如貨物賣不出。
從前驚恐又貧困,與你共同渡艱難。
如今豐衣又足食,你卻把我當害蟲。
我處存有美菜肴,留到天寒好過冬。
你們新婚樂融融,卻讓我去擋貧窮。
對我粗暴發怒火,辛苦活兒全給我。
從前恩情全不顧,你曾對我情獨鐘。
賞析:
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就是一個獲得平衡的問題。正如時髦話說的,人字的結構就是相互支撐。少了另一半,這一半就失去平衡垮掉了。夫妻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夫妻各撐半邊天,“人”字就樹立起來了,家也就有了。
問題在於,取得平衡容易,保持平衡長久不變困難。
常言說,天下沒有不吵架的夫妻。夫妻的爭吵可以在兩個層面上進行:在具體的、有形的、物質的層面上爭吵,比如為鍋碗瓢盆油鹽醬醋撫養子女孝敬公婆之類;在……理的、無形的、精神的局面上爭吵,比如為性格衝突、觀念差異、精神追求之類。可以說,這兩個層面大的任何一種爭吵,都有可能導致夫妻反目,分道揚鍍,形同路人,視若仇敵,至死不相往來,甚至加害於曾經親女。手足的對方。
也可以說,天下最親密的關係是夫妻關係, 而天下最危險、最脆弱的關係也是夫妻關係。
然而,同“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不一樣的是,對夫妻關係最大的威脅和危險是來自外部,來自外部力量的誘惑。夫妻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上的爭吵導致“人”字解體、平衡喪失,需要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在時間過程中多次的重複。一兩次爭吵不足以構成威脅,兩三次、三五次甚至也不會有根本的妨礙,都還有妥協、緩和、補救、修好的迴旋餘地,都還可以退後一步天地寬。來自外部的威脅和誘惑,可以迅速地從根本上瓦解“人”字的平衡。這種致命的炸彈,常常就是另外一個具有擋不住的誘惑力的異性。他或她出現在夫和妻之外,從外部吸引著婦或夫,先形成三角形,然後是一個“人”字垮掉,另一個“人”字搭起來。如今,這已是我們習以為常、司空見慣了的情形。對此無論是褒是貶,反正在一天天發生,還一天天多起來,地球也照樣在運轉。這些都是後話。時光倒流百年、千年,與如今應當有很大的差別。那時,人與人之間,夫與妻之間有種種維護其間關係的規則,也就是被稱為“道德”的東西。這些規則不能說不嚴格,但卻不能說是平等的。比如妻子,她不是獨立的,要依賴于丈夫。而丈夫可以不依賴妻子,甚至可以擁有妻子之外的妾。這樣一來,規則對丈夫移情別戀網開一面,為夫妻關係遭受威脅和危害留下了一道不設防的地段。關係焉有不失去平衡的保證。
唯一剩下的東西,就是內在的“良心”了。可是,良心也是非常脆弱的,即使有朝夕相處建立起來的“一日夫妻百日恩”,也難以抵禦新人的誘惑。
所以,昔日的妻子被拋棄,道德規則本身就負很大一部分責任,播下了悲劇的種子。棄婦,便是由這種子開出的幽怨的花朵。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遊”,猶言作長夜之遊。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呢!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遊!——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歎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而天下最危險、最脆弱的關係也是夫妻關係。然而,同“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不一樣的是,對夫妻關係最大的威脅和危險是來自外部,來自外部力量的誘惑。夫妻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上的爭吵導致“人”字解體、平衡喪失,需要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在時間過程中多次的重複。一兩次爭吵不足以構成威脅,兩三次、三五次甚至也不會有根本的妨礙,都還有妥協、緩和、補救、修好的迴旋餘地,都還可以退後一步天地寬。來自外部的威脅和誘惑,可以迅速地從根本上瓦解“人”字的平衡。這種致命的炸彈,常常就是另外一個具有擋不住的誘惑力的異性。他或她出現在夫和妻之外,從外部吸引著婦或夫,先形成三角形,然後是一個“人”字垮掉,另一個“人”字搭起來。如今,這已是我們習以為常、司空見慣了的情形。對此無論是褒是貶,反正在一天天發生,還一天天多起來,地球也照樣在運轉。這些都是後話。時光倒流百年、千年,與如今應當有很大的差別。那時,人與人之間,夫與妻之間有種種維護其間關係的規則,也就是被稱為“道德”的東西。這些規則不能說不嚴格,但卻不能說是平等的。比如妻子,她不是獨立的,要依賴于丈夫。而丈夫可以不依賴妻子,甚至可以擁有妻子之外的妾。這樣一來,規則對丈夫移情別戀網開一面,為夫妻關係遭受威脅和危害留下了一道不設防的地段。關係焉有不失去平衡的保證。
唯一剩下的東西,就是內在的“良心”了。可是,良心也是非常脆弱的,即使有朝夕相處建立起來的“一日夫妻百日恩”,也難以抵禦新人的誘惑。
所以,昔日的妻子被拋棄,道德規則本身就負很大一部分責任,播下了悲劇的種子。棄婦,便是由這種子開出的幽怨的花朵。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遊”,猶言作長夜之遊。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呢!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遊!——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歎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