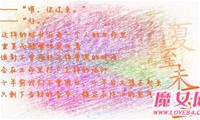《詩經:采蘩》
於以采蘩?于沼於沚。
於以用之?公侯之事。
於以采蘩?於澗之中。
於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
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注釋:
1、於以:到哪裡去。蘩:水草名,即白蒿。
2、沼:沼澤。氵止:小洲。
3、被:用作“皮”,意思是女子戴的首飾。僮僮:童童,意思是首飾繁多。
4、夙夜:早晨和晚上。
5、祁祁:首飾繁多的樣子。
譯文:
到哪裡去采白蒿?在沼澤旁和沙洲。
白蒿采來做什麼?公侯拿去祭祖先。
到哪裡去采白蒿?在那深深山澗中。
白蒿采來做什麼?公侯宗廟祭祀用。
頭飾盛裝佩戴齊,從早到晚去侍奉。
佩戴首飾真華麗,侍奉結束回家去。
賞析:
到野外去采白蒿,在祭祀場所守侯侍奉,肯定不屬於王公貴族們幹的事。做這些事的,只能是下等的僕人,而且是女僕。
千辛萬苦到野外采來白蒿,是供王公貴族祭祀用;費心勞神打扮裝點,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為誰辛苦為誰忙?全是為他人做嫁衣裳。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滋味如何?唯有女僕內心體驗最深。雖然沒有言說,我們卻感到似乎平淡的敘說中有幾分怨忿在。
為他人做嫁衣裳,意味著自我不存在,自我變成了他人的工具。奴僕供人差遣使喚,本就是人為事先設定的,似乎像“命運”決定的。即使不是奴僕,人生都免不了有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時候。自覺自願,並引以為自豪地為他人 做嫁衣裳,是犧牲精神和奉獻意識的體現,
如今我們可以拒絕被迫為他人做嫁衣,但在很多情況下是無法拒絕的。比如受老闆雇傭,老闆叫去陪酒,明知不勝酒力卻又不得不去。重賞之下必有勇副,是看准了人心追名逐利的弱點,抓住弱點使人為別人做嫁衣。
認真想來,做人是擺脫不了為他人做嫁衣的處境的。區別僅僅在於:是自覺的,不自覺的和被迫的。
《詩經:何彼襛矣》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注釋:
1、襛(音濃):花木繁盛貌。
2、唐棣(音地):木名,似白楊,又作棠棣、常棣。一說指車帷。
3、曷(音何):何。
4、肅:莊嚴肅靜。
5、雝(音擁):雍容安詳。
6、王姬:周王的女兒,姬姓,故稱王姬;一說為美女的代稱。
7、平王、齊侯:指誰無定說,或謂非實指,乃誇美之詞。
8、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是婚姻戀愛的隱語,或指男女雙方門當戶對、婚姻美滿;或指用適當的方法求婚。
9、維、伊:語助詞。
10、緡(音民):合股絲繩,喻男女合婚;一說釣繩。
譯文:
怎麼那樣穠麗絢爛?如同唐棣花般美妍。
為何喧鬧不堪欠莊重,王姬出嫁車駕真壯觀。
怎麼那樣地穠麗絢爛,如同桃花李花般嬌豔。
平王之孫容貌夠姣好,齊侯之子風度也翩翩。
什麼東西釣魚最方便,撮合絲繩麻繩成釣線。
齊侯之子風度也翩翩,平王之孫容貌夠嬌豔。
賞析:
《何彼襛矣》一的主旨,《毛詩序》以為是“美王姬”之作,雲:“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也。”古代學者多從其說,朱熹《詩集傳》也說:“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美之。”近現代學者大都認為是譏刺王姬出嫁車服奢侈的詩。高亨《詩經今注》卻認為是“周平王的孫女出嫁于齊襄公或齊桓公,求召南域內諸侯之女做陪嫁的媵妾,而其父不肯,召南人因作此詩”。袁梅《詩經譯注》又持新說,以為是男女求愛的情歌,詩中的“王姬”、“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不過是代稱或誇美之詞。我以為此詩是為平王之孫與齊侯之子新婚而作,
全詩三章,每章四句,極力鋪寫王姬出嫁時車服的豪華奢侈和結婚場面的氣派、排場。首章以唐棣花兒起興,鋪陳出嫁車輛的驕奢,“曷不肅雝”二句儼然是路人旁觀、交相讚歎稱美的生動寫照。次章以桃李為比,點出新郎、新娘,刻畫他們的光彩照人。“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二句雖然所指難以確定,但無非是渲染兩位新人身份的高貴。末章以釣具為興,表現男女雙方門當戶對、婚姻美滿。
“通篇俱在詩人觀望中著想”(陳繼揆《讀詩臆補》),全詩在詩人的視野中逐漸推移變化,時而正面描畫,時而側面襯托,相得益彰。從結構上說,全詩各章首二句都是一設問、一作答,具有濃郁的民間色彩,“前後上下,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遊”,猶言作長夜之遊。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呢!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遊!——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歎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這是何苦呢?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呢!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遊!——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于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歎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裡,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于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餘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遊”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歎,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